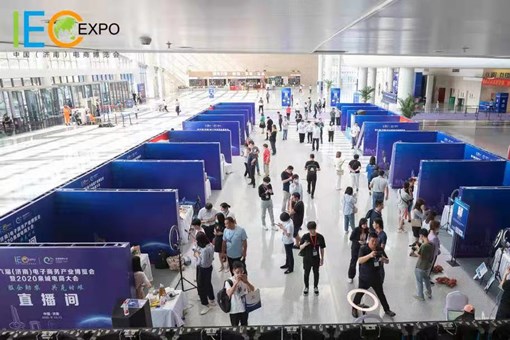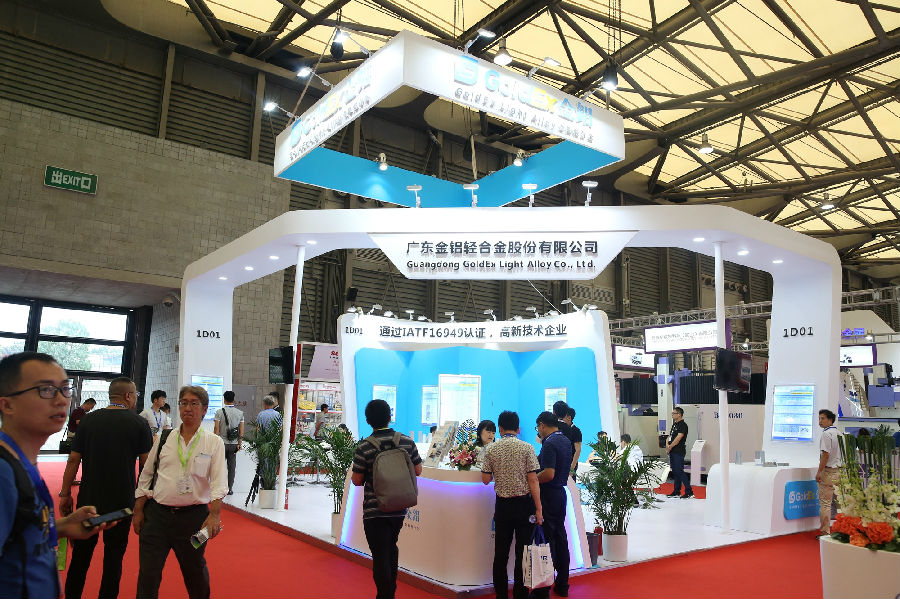(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10期。原文约12000字,题目为《“未来”的观念变迁及其传播思想史面向》。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
尽管迷思反复终结,但这套技术乐观主义的未来话语却在人工智能、大数据、自动驾驶等新兴技术领域不断“复蹈前辙”,这不仅因为技术已经成为现代性中最为坚固的意识形态之一而难逃其解放框架,还因为当动用这套熟悉的观念和话语资源时总是其验如响。“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概念在近些年来的广泛运用也表明了,社会秩序和文化所塑造的集体想象在科学技术设计与践行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数字技术与想象未来的联系也被社会学视为具有整合潜力的研究主题。2021年,《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发表专刊“‘我们肩负使命’探索数字技术创造和管理中的未来想象”,追溯了未来愿景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出现,它们如何跨越时间、空间和领域获得力量,又如何相互竞争和互补,以及与替代性的未来争夺主导地位。在这里,未来愿景的以言行事功能、力量及其表演性再次得到了强调。“通过引导对未来事物和服务的创造,未来的想象正在共同生产他们所设想的未来。”
科幻文学笔下的未来想象不见得都是世外桃源式的大同社会,乌托邦文学衍生而出的反乌托邦倾向在科幻文学领域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观照未来的另外一面镜鉴。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电影《机械姬》以及英剧《黑镜》等,揭示了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甚至部分已经成为现实的科技的黑暗一面。在此,未来是已知和确切的,但其许诺的人类命运又是开放的。如果说科幻重启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那么反乌托邦文学则充分体现了这种未来想象背后的“幽暗意识”,即窥探各种理想或是理性的疆界以外的不可知或不可测的层面,也是探触和想象人性和人性以外、以内最曲折隐秘的方法。
从更长的时间脉络来看,信息传播技术的未来想象与工业时代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它延续了萌芽于17世纪欧洲、形成于19世纪美国的技术乌托邦主义(technological utopianism)的技术进步意识形态,认为技术进步永远有利于社会甚至等同于社会与人类进步。工业技术的发展以及原本不切实际的乌托邦逐渐成为了可能,这两种趋势相互交织,并在19世纪的美国率先合流。西格尔(Howard P. Segal)列举了《新纪元》《公元2000年》《展望未来》等25部技术乌托邦主义作品,大部分作品都提供了明确的未来社会蓝图,即将技术视为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出路——这是此前的乌托邦作品中所不曾出现的。在这些作品中,技术被赋予幸福、繁荣、民主等积极的意识形态意涵,其所带来的问题只是暂时的,并乞灵于更加进步的技术加以解决。
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未来”,在语词形式上就构成了一种有趣的矛盾——通过“未来”理解过去?未来几乎存在于从古至今所有社会的前景想象中,这不足为奇,毕竟,人都会在有意无意间期待、展望自己及社会的前途。但未来不只是个体的心理愿景或集体的社会想象,它也可能成为一项工具、一种观念体系乃至一种意识形态。未来不仅能够映照当下,展现出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思想模式和情感结构,它同时也构成社会行动的价值参考和目标。本文尝试梳理“未来”观念的历史变迁,并落脚在传播研究中的“未来”面向,探索“未来”观念在(广义及狭义)传播思想史中是否还存在有待开掘的理论空间。
作为一种观念,“未来”的概念意涵可以表述为“此刻往后的时间”,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使用“未来”的语境、范畴以及相应未来观却大不相同。本文在此试图勾勒出三种世俗世界中未来的“寄寓之所”,以呈现未来观念的历时性变化。
与乌托邦密切相关的另外一种想象未来的重要方式是科幻文学。它萌芽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19世纪,在清末被引介到中国,在动荡的时局中有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康有为的《大同书》、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等,均以无限乐观的心态描绘了技术助力下的美善之地。晚近则有斩获雨果奖的刘慈欣《三体》、郝景芳《北京折叠》,带动了以科幻为主题的电影、杂志、文化媒体等科幻文化生产链的蓬勃发展。
虽然同样都是指向整体的社会现实,乌托邦中的“未来”与古代传统中的“未来”却有很大不同。乌托邦表达的并不是预先给定的未来,而恰恰相反,它是作为一种几乎不能实现的替代方案而出现的。饶是如此,乌托邦仍然有强大的吸引力,在于它至少有三种不一定互斥的功能:第一,补偿,即将幻想作为逃离现实的避难所,而不必改变外在世界;第二,批判,通过构建理想化的目标,否思我们所置身其中的现实世界;第三,催化,即在批判的基础上催化现实世界的变革,创生美好进步的替代世界。
时至今日,国内新闻传播研究仍然带有鲜明的“未来”时态:研判技术变革的走向及其社会影响,已成为新闻传播学术写作的一类重要范畴。托夫勒、奈斯比特、尼葛洛庞帝等未来学家的预言式论述频繁出现在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中,成为或隐或现的对话者;与未来主义“过从甚密”的麦克卢汉也一直是国内传播学的重要思想源泉。有学者发现,国内新闻传播领域的人工智能研究“热点效应”尤为明显,而国外学者并不热衷关注新技术。
未来不仅能够映照当下,展现出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思想模式和情感结构,它同时也构成社会行动的价值参考和目标。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方惠在《传媒观察》第10期刊文,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未来”的三类观念星丛:神文主义的谶纬和占卜、乌托邦以及科幻文学,并着重论述了19世纪以来未来观念发生的重大变化。晚近以来的未来观念在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中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未来的冲击》等未来学著作将信息视为社会变革的驱动力量,这种未来观念的影响力迅速蔓延全球,也深刻影响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进程以及新闻传播的学科范式。在工业浪潮以来的“未来”想象、未来主义思潮在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未来”倾向等主题上,未来主义都给传播思想史带来了丰富的议题资源和有待清理的思想遗产。
从狭义的传播学术史角度,未来主义思潮也曾引发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虽然托夫勒等人似乎并没有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产生直接交集,但其影响却是沿着自上而下的发生学路径——说服高层形成政策导向,进而凭借广义的社会气候引起新闻传播学关注。尽管在未来主义思潮之前,实证研究和批判视域的“信息”概念均已进入学界视野,但却始终面临着资本主义舶来品的“合法性赤字”。传播学者也惊讶地发现,他们艰难推广的实证研究中的“信息”居然摇身一变成为了风潮:“‘信息热’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但研究信息交流的传播学仍在艰难地前行,几度因为‘舶来货’的声名而遭侧目。”在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信息的政治性被置换为科学性,成为新闻改革的路径和目标以及助推新闻传播学走向现代化的良方,而传播学者的使命,也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为即将到来的信息社会做准备,从而具备了政治战略上的高度。
以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为代言人的未来主义思潮被引介进入中国,恰逢中国旧有的未来许诺主张遭遇挑战的时刻,“新技术革命”被有选择地和马克思对于生产力的分析嫁接在一起,成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在信息时代的继承人。1970年代末,作为“三学”之一的未来学因倡导科学地预测和控制未来发展而受到国家科委的重视,1979年,中国成立未来研究会。1981年,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节选被翻译连载于《读书》,1983年初,托夫勒夫妇访华,并受到政界和学界接待;同年,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也被引介至国内。很快,国务院召开新技术革命座谈会,商讨如何应对新的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在经历短暂的意识形态争论后,“新技术革命”“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等未来主义论断被中国官方所采纳,它为当时刚刚摆脱斗争、谋求发展的中国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未来主义”(actionable futurism),并推动了一系列科学技术政策以及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的出台。
解梦、预言、占卜等连接未来的方式在巴比伦、埃及、波斯等人类早期文明中也广泛存在。这些传统共享着相似的未来观:首先,未来是预先给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通过适当的方法可以提前知晓;其次,普通人获知未来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们需要不断练习或借助外部力量来解读昭示未来的种种迹象。于是巫师、占星师、通灵者等成为未来知识的权威代理,可以说,确定性和神秘主义是这种未来观念的关键要素。
尽管未来主义在生态、城市、环境、艺术等方面均有体现,但近半世纪以来,其最有影响力的分支当属以信息技术等为基础的未来学论述,集中体现在布热津斯基《电子技术时代的美国》(1967),托夫勒《未来的冲击》(1970)、《第三次浪潮》(1980)、《权力的转移》(1990),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1979)等未来学家的著作中。这些预测都以突飞猛进的科技革命为出发点,描绘了“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电子技术社会”等交织着希望与欲望的人类生存方式。
几乎所有探寻未来的努力都可以追溯到远古。中国秦汉以前就有“立言于前,有征于后”的“谶书”,它与“纬书”一道,构成了中国最具神秘色彩的叙事话语。谶纬在中国古代王权争夺、军事行动、政治更迭等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谶纬之学在两汉三国时期登峰造极。汉武帝刘秀通过编纂和发布图谶使其经典化,促进了谶纬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传播。背后体现了先民朴素的未来观念和信仰体系,即将超验而可感的现象与社会或人生的结果建立起因果关系,人类世界是天命秩序的反映,而天的意志可以通过谶验星象变化、五行征象、占卜、梦境等超自然现象来预测和解释。
“未来”观念在近一两个世纪以来的语境变得更为复杂,且与传播研究的关系越发紧密。它经历了科学化的转向,不仅要求科学作为论述对象,也强调运用科学方法,未来预测甚至一度在高校被建制化。这都意味着未来不再是正在生成(becoming)和有待填充的,而是被视为切实存在着的社会事实。更具体来说,与信息传播技术的接合作为当前未来主义最具影响力的分支,延续了工业时代以来的技术乌托邦愿景,但经过了控制论视域的重新塑造,将信息看作新技术革命的神圣系统。这种未来观念的影响力迅速蔓延全球,也深刻影响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进程,以及新闻传播的学科范式。传播研究的未来关切体现在于其对于媒介技术及其影响的不舍穷追,一种是人文主义的路径,批判性地探查未来想象/叙事在数字技术发展过程的角色及其相互影响。这一路径已经硕果累累,甚至溢出本学科而成为社会学知识生产的潜在重要分支。另一种则是未来主义的路径,传播研究者自身深度参与到了未来预测的行动之中,这是政治、商业之外另一种权威配置的过程,且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其方法论上的可行性及其现实效用仍值得进一步讨论。
在未来主义思潮本土化的过程中,科技企业及其代理人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迷思几乎是所有商业推广与宣传的共性,因而技术决定论式的观念在商业话语中最为常见。有研究发现,早期IT领袖们利用充满未来色彩的信息话语想象现代性的可能形式,以使西方科技融入本地的社会发展,这种对于技术的想象塑造了其发展方向和模式,使得信息社会的未来图景越来越多地和商业与市场联系在一起。2023年9月,在《时代》首次发布的全球百大AI人物中,百度CEO李彦宏被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未来主义者”。未来主义与科技企业的结合不是偶然,两者的理念如出一辙——“真正推动这个社会进步的还是算法,还是技术。”而前者半学术化的自由写作为后者的商业公关提供了最肥沃的话语土壤。
考斯莱克将“未来”概念视为现代性的时间基石。一个特定的时代越是被体验为一种新的时间性(即“现代性”),它对未来的要求就越高。在时间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的全球社会,如何应对“未来”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回应。除了上述社会学者之外,人类学家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提出人类学应当将“未来”视为一个文化事实(cultural fact)来研究,它不是纯粹中立的或者技术性的,而伴随着敬畏、眩晕、兴奋、厌恶等不同情感空间。想象(imagination)、预测(anticipation)和渴望(aspiration)的能力是一种文化能力,需要系统地理解作为规范、意向、实践和历史组合的文化系统是如何把美好生活塑造成一种可辨目的和途径的。
信息传播技术的未来想象以热衷进步的技术乐观主义为基调,通过调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中相关资源,认为电脑传播的力量具有超越时间(终结历史)、空间(终结地理)和权力(终结政治)的潜力。通过崇高许诺的叙事,让人们得以超越平庸的日常,通向另一种现实。这种信息社会的主导愿景几乎构成了一种“知识垄断”,凌驾于其他倡导良好社会的愿景和实践之上,其结果带来了互联网在当代社会的全面制度化。
在文学、政治学以及哲学的研究传统中,乌托邦是一个重要主题,它可以追溯到1516年托马斯·莫尔的名作《乌托邦》。乌托邦的创作母题衍生出了社会乌托邦、政治乌托邦、地理乌托邦等多个类型,究其本质,曼海姆曾给“乌托邦”下过一个简单的定义,即如果一种思想与产生这种思想的现状格格不入,这种思想就是乌托邦式的。不可实现性构成了乌托邦的重要特质。事实上“乌托邦”概念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战场,通过贴上“乌托邦”的标签否定对手要求的有效性。